为传承和发扬舒城本地的优秀文化,解读记忆中的舒城民风民俗,彰显深厚的龙舒文化意蕴,感知千年龙舒文化血脉的起伏脉动。由中共舒城县委宣传部编撰的《记忆中的舒城民俗》一书于2024年9月出版发行。书中收录了舒城本土的时令节庆、喜庆礼仪、丧葬祭祀、农耕渔猎、衣食住行、饮食文化、文化娱乐、童趣游戏等风俗民情。为此,中共舒城县委宣传部和舒城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开设《记忆中的舒城民俗》系列专栏,分享书中的文章,与您一起品味舒城的风俗民情,感受龙舒文化,敬请关注!
“铁环英雄”练成记
丁文新
“小文子,不要急,我来把你想点子。”每当爷爷慢条斯理地吐出这句话时,我的沮丧便跑掉了一大半,这次,爷爷给我承诺的是一副铁环。而与此相反的,是母亲的指责:“你看看,这么多玩具,还要那么多干啥?”“都是一些拿不出手的东西。”我在心里嘀咕着,一边无奈地瞅着桌上那些一言不发的玩具,有跳绳、毽子、抓石子儿、弹弓、打宝、纸飞机等,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。那个年代,学习似乎并不那么重要,小伙伴们之间交流最多的是一件又一件的玩具、一个又一个游戏。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样,但却让我们乐此不疲。一开始是凑在一块玩玩闹闹,消磨时间,当后来上升为所谓的比赛时,这些配置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。毽子容易,对于两个姐姐来说可谓是手到擒来。找两块铜钱叠在一起,在孔眼里塞进一根塑料管子,用针线扎紧,里面插上鸡毛,便大功告成。如果想美一点,可以在鸡毛上面抹几滴桃红,便更加显眼了。橡皮筯、跳绳就更容易,俯首即是,更不用说那打宝、抓子儿了。而这次,铁环却成了难题。在打宝、抓子儿、跳房子这些不需要什么成本,这些没挑战性的游戏玩腻了之后,滚铁环成了我们的最爱。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男孩子,就是速度和技术的较量。看到小伙伴滚铁环时那副得意洋洋、大呼小叫的神气劲,我眼红了,这铁环、铁钩从哪来呢?父亲除了叫我写作业、打猪草、喂鱼、捡鸡粪外,其它的一概反对;一年到头忙得脚不沾地的母亲是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的;爷爷最疼我。“爷爷,我要滚铁环。老师说,这次运动会要加上滚铁环比赛。”我觍着脸,在爷爷面前哼哼唧唧着,表现很无赖的样子。“来来,这个容易。”爷爷略略思忖了一下,来到堆满家具、农具和杂物的屋子里,从黑黝黝的角落里挪出了我们儿时用过的布满灰尘、灰不溜秋的站桶。爷爷用一个凿子沿着站桶中间位置用来固定桶身的铁箍,一寸寸地往下砸,“咣当——”铁箍落地,我的铁环诞生了;接着,爷爷找来一根粗铁丝,用钳子左抻右扭,铁环钩子便做成了。“滚铁环喽,滚铁环喽!”我即刻上手,飞奔至生产队宽敞的场基上,在那些正玩得兴高采烈的小伙伴面前,趾高气扬起来。多少天以来的郁闷、自卑一扫而光。当时,我能感觉到爷爷在我身后那眯起的笑纹和不时颤抖的山羊胡子,还有同伴们羡慕的目光。我的第一个铁环,让那一刻的童年充满了光亮。当然,还有最闪光的时刻——那次学校运动会上,在滚铁环比赛当中,我获得了第一名。“铁环英雄”的光荣称号让我美了好长一段时间;这也成为此后爷爷逢年过节、茶余饭后向亲戚朋友炫耀的话题。之后,不记得爷爷又帮我做了多少副铁环。在与小伙伴们一次次的追逐和竞赛中,不论是放学路上,还是狭窄的河道旁,我的铁环在冲锋陷阵中,不是跌入了水塘,就是栽下了山坎。每次丢失了铁环,爷爷总是想方法为我再做。家里的火桶,水桶,腰桶等,凡是有箍的都被爷爷取了下来。最后东窗事发,父亲的责问,母亲的唠叨,都被爷爷大义凛然地扛了下来。后来,爷爷找了一个铁块,走了好几里路,送到邻村的铁匠铺里,叫铁匠师傅给我打做了好几副铁环,爷爷为了付给我做铁环的工钱,卖掉了他抽的烟叶。滚铁环成了我童年最闪光的记忆,也让我更加怀念我的爷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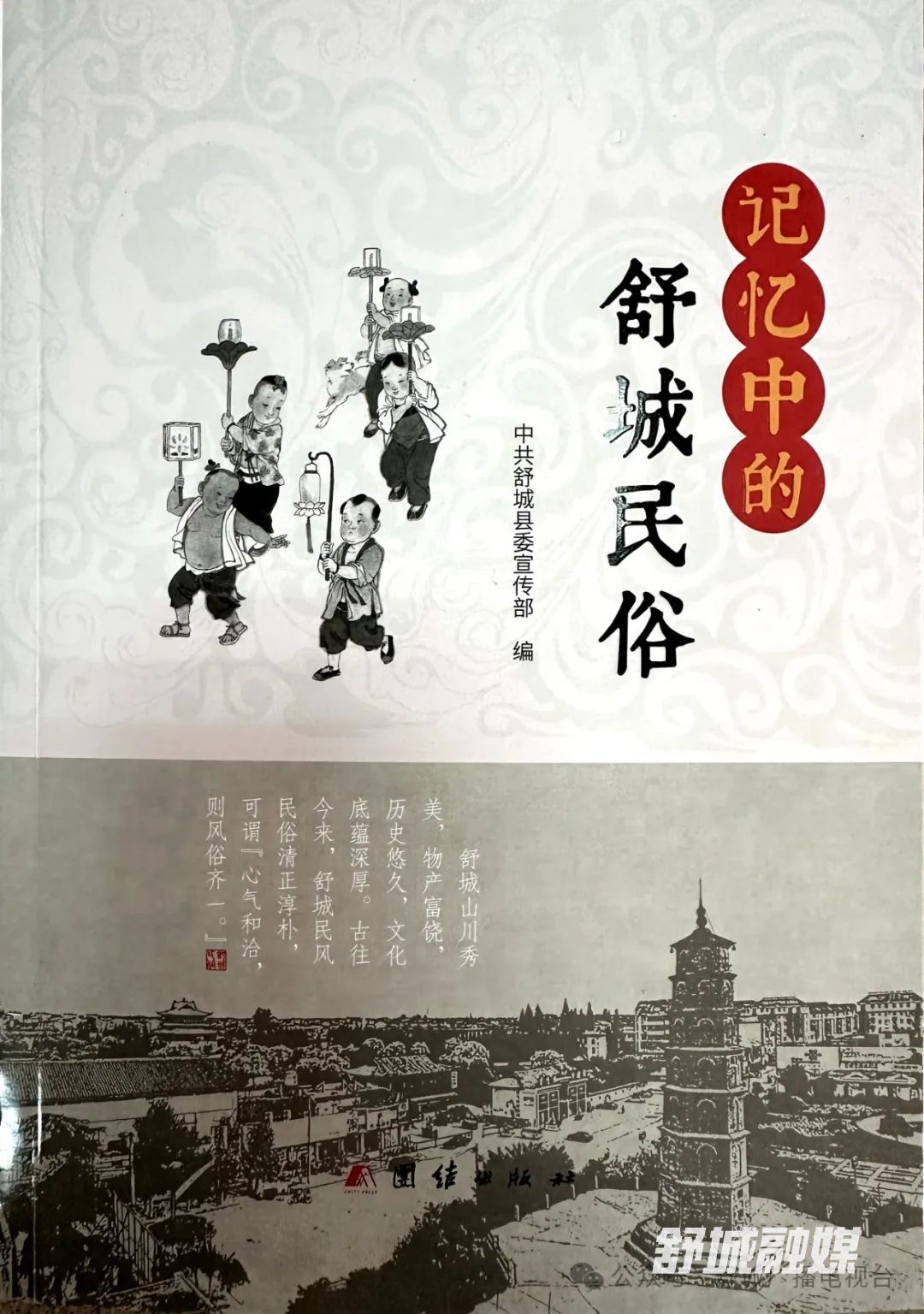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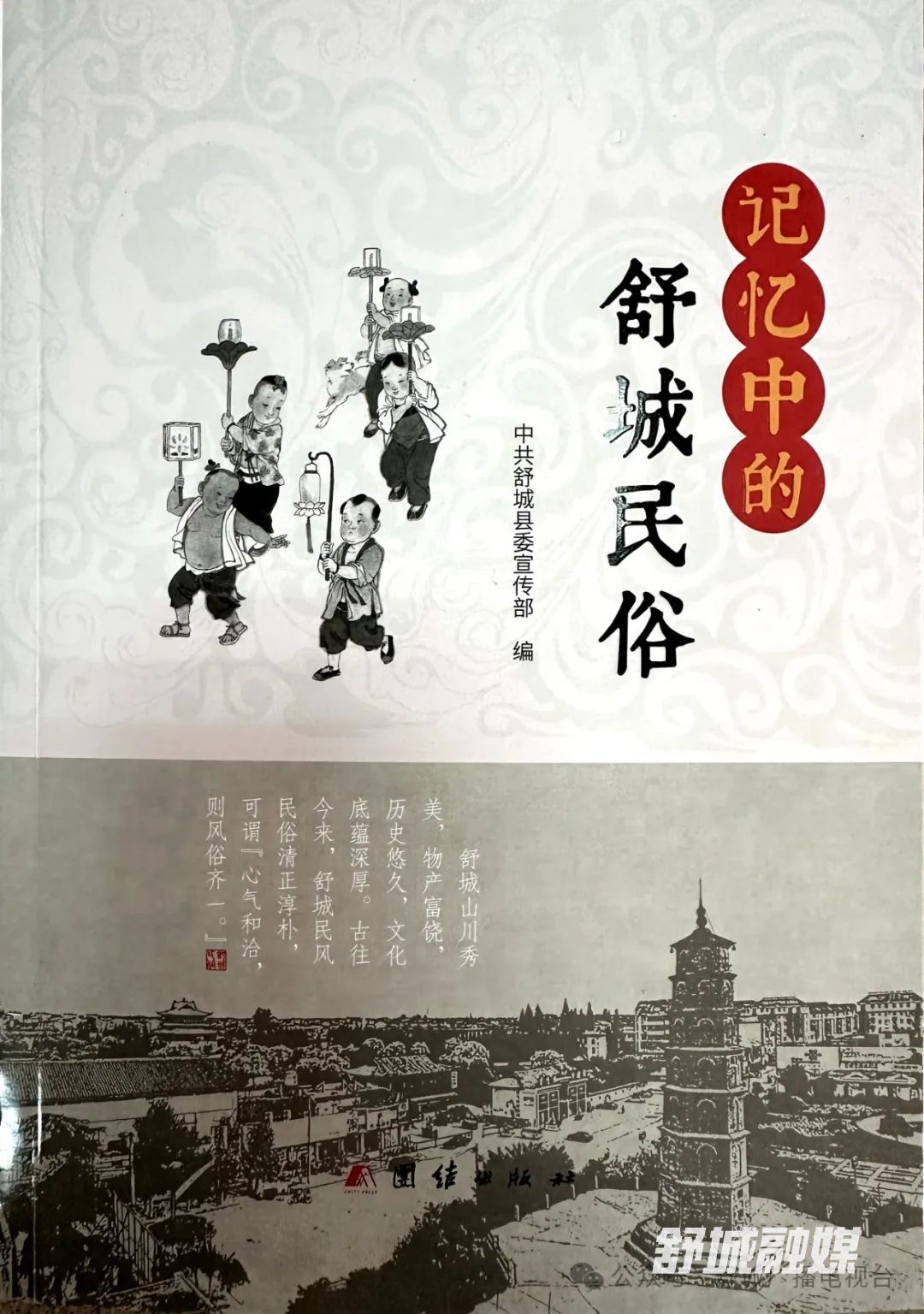
 皖公网安备 34152302000107号 技术支持:舒城传媒 访问统计 次
皖公网安备 34152302000107号 技术支持:舒城传媒 访问统计 次